文音寄來的信,主旨總是很簡短。點開信件,看著她言簡意賅的交代,我用時間培養出的默契解讀。
文音會是編輯喜愛的作家。她往往將稿件、照片,整理得俐落後,才交到編輯手上,讓編輯在編務工作開始前,就能充分明白新作的邏輯與意旨。這是謹慎,也是體貼。
身為編輯的我,自然而然對她的作品產生敬意,不敢輕忽。
台灣百年物語二部曲《短歌行》與首部曲《豔歌行》,出版時間相隔三年。這三年來,文音並未鬆懈寫作,出版了《三城三戀》、《少女老樣子》、《大文豪與冰淇淋》、《慈悲情人》幾部作品。或是旅遊散文、或是小說,每本書都是她這些年來一段經歷的沉澱。
對文音的忠實讀者來說,書中這些旅途筆記與思路的轉折,都是滋長他們更加熱愛文學的養分。作為台灣文學界壯年作家的代表,文音的文體有著高密度的細膩,感性但不矯情,並兼有視野與觀點。從編輯的眼中看來,寫作對文音來說,是天生就會的,是許多有心從事文藝創作的人,渴望但不可得的才華。
這幾年來,文音的創作野心是長篇大河小說。她以台灣這塊土地為舞台,以台灣人的際遇作為劇本,計畫先以三部巨著來書寫百年台灣,它們分別是:《豔歌行》、《短歌行》與《傷歌行》。
《豔歌行》說的是1989年後,台灣男女的青春豔事。她以30萬字的重量,書寫台北城裡的情色逸樂,如何與慾望拉鋸,如何對抗城市這具看似與住民關係緊密、實則疏離的無情機器。
有人說,文音將「豔事」寫得太長。但文音說:「不寫那麼多的豔,不足以寫出『豔』後的『腐朽』,最好是讀到『豔』的極致而產生『厭』的嘔吐感。如此很符合當代人的情色眾生相。」
當代都會裡,每個人都是座孤島,每一段關係都如緊繃的絲絃、張力過大即告斷裂。在《豔歌行》裡,人與人之間,沒有永恆的風景。城市的地貌也是,舊地標的拆遷,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;新建物的誕生,刺痛了戀舊者的眼。
「我知道這一切終將成廢墟,但我並沒有要永恆啊。」《豔歌行》裡,這段話是個刺點。城市男女,哪個相信真有永恆?只有將青春不斷延長,與情愛肉搏。
相對於《豔歌行》中當代男女青春之「長」,《短歌行》談論的,則是青春之「短」。
《短歌行》從1920年代書寫至2009年,將時空從近代拉至當代,「不截斷小說敘述的時間之河」。文音想表現的是歷史的「意外」與「荒謬」,以及「人的際遇」瞬息萬變。
80多年的時間之河,在台灣這塊土地上,有著幾次歷史大轉折──從日本殖民時期,轉入了由蔣中正主導的國民黨統治時期,二二八事件,白色恐怖,蔣經國宣布解嚴,總統民選,政黨二次輪替……國土的際遇如此多變,連帶也影響了土地上的人民的際遇。
文音在《短歌行》裡,以「鍾」姓與「舒」姓這兩個家族中男性成員的人生跌宕,導引出她想談論的「青春之短」與「際遇多變」。
青春為何短?因為難以治癒的疾病;因為無法預知的天災;因為忠於心中理念去對抗當權,而提早結束了青春;因為愛情,往往短暫。
際遇何以多變?人的際遇,與時代息息相關。當時代動盪、當人心恐慌,所有人的際遇,都會更增添不確定。
至於即將在2010年秋冬出版的三部曲《傷歌行》,則更將時間座標拉長。從1895年甲午戰爭前後,書寫至2010年,且與《短歌行》的男聲區隔,以「女腔」發聲。文音將以《短歌行》裡鍾家四個太祖婆拉開歷史序幕,最後以「鍾小娜」為終曲。
擅長寫「女性」的文音,據悉將《傷歌行》裡的一幕幕女腔寫得淋漓盡致,且已接近完稿階段。身為編輯,對於在不久的未來就能盡情讀稿這事,十分期待。
百年物語三部曲彼此間故事雖未連貫,但文音安排了「鍾小娜」這號人物,貫穿其中。除了透過小說中人物的視角鋪陳故事,有時也會讓鍾小娜的視角出場,使小說整體結構更具層次,也讓三部曲不致潰散。因此,三部曲可不分出版順序,任意讀之,也可依序閱讀。
那位「鍾小娜」,就是文音嗎?文音說:「我總是不吝惜讓『我』介入小說世界裡,由於『我』的『近距離』發音,以至於很多人覺得我寫的都是『真實』的事。」
「實」與「虛」交錯,構築成文音的小說魅力。
至於何者為真、何者為假,不必猜,也不必問。
《豔歌行》是我編文音的第一本書,三年多時光過去,來到《短歌行》。
至今還記得初見文音時,看著她走進大田辦公室,我心中的忐忑(面對作家從文字裡走到現實,我總是忐忑)。長長直直的頭髮,異國風情的服飾,具有穿透力的眼神。她用低沉嗓音慢慢說話,嘴角有一抹淺淺的笑,耐心地與我討論著照片與封面的選擇……我那時想起多年前讀著她的《過去》,那些書裡的文字,陪伴我度過一個天空不晴、適合緩慢的假日下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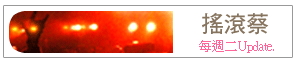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